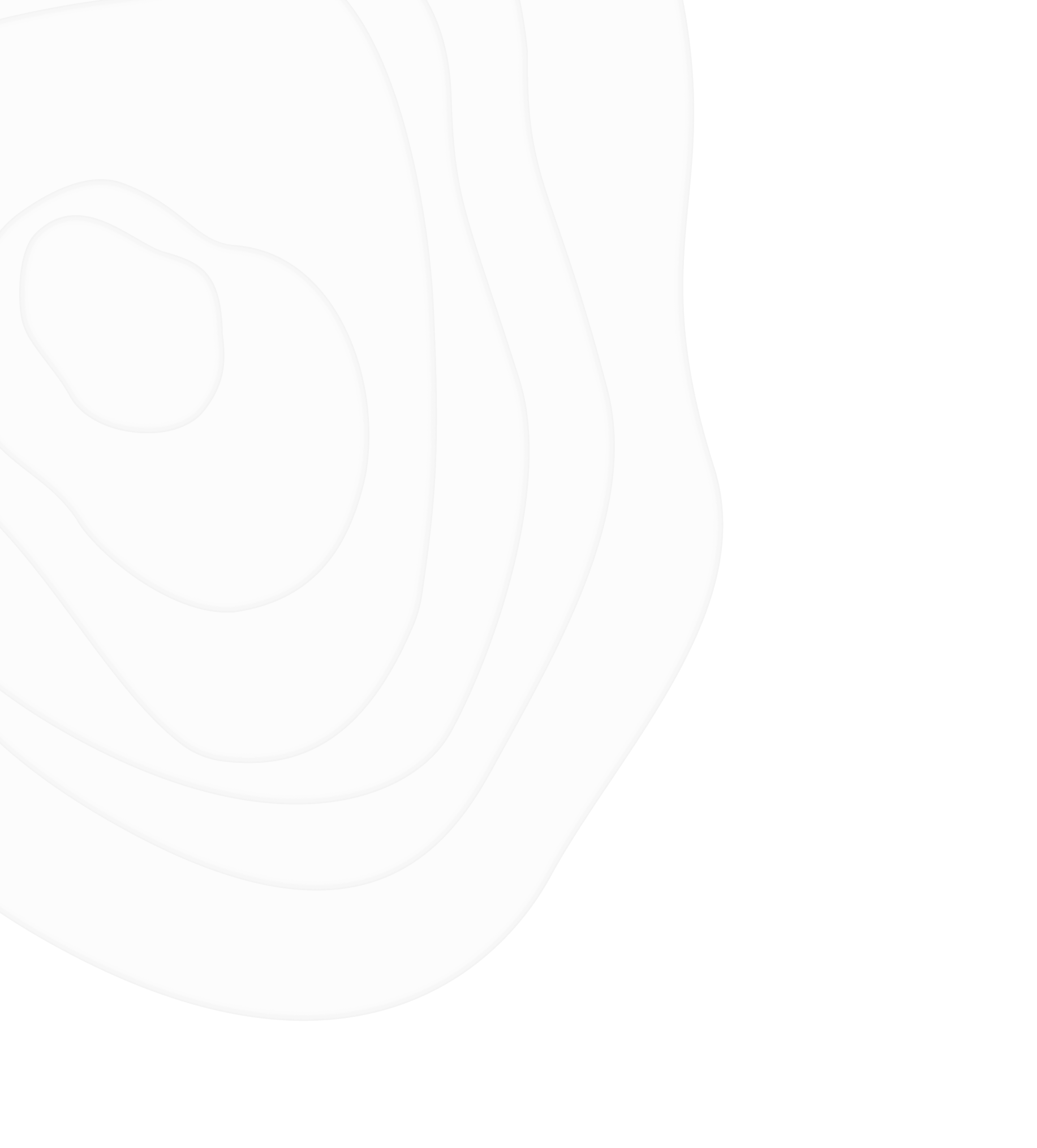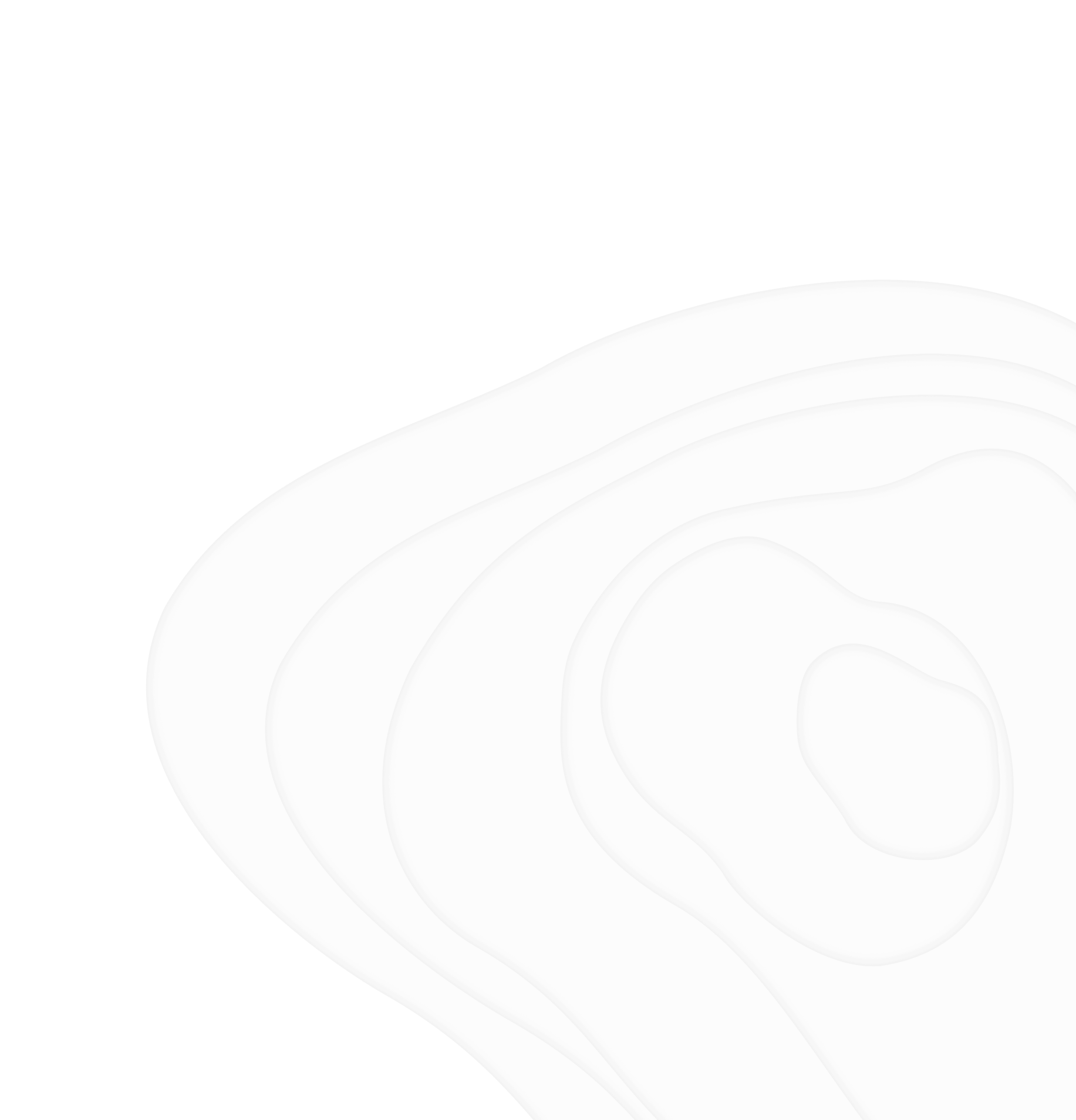WORK工作人
Tag
Share
⸺專訪自然系音樂創作者 雷擎
從生活與自然出發的聲音創作
文|編輯部
圖片提供|雷擎、子皿有限公司|插畫 @sun_zoeee
你覺得「文化」和「自然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,跟自己的生活沒什麼關係嗎?但對於喜歡觀察自然、記錄夢境的音樂人雷擎來說,這些可不只是知識,而是每天都能接觸、感受的靈感來源! 在他和LINION合作的歌曲〈Mountain Dude〉裡,你會聽到木頭、石頭的敲擊聲,或是利用果實在乾濕不同的狀態,帶出不同的畫面感;透過環島旅行找尋靈感的專輯《Dive & Give》,可以聽見各種溪流、沙子、石頭的聲響,把臺灣的自然景色融入音樂;《南洋探險隊》,則帶著樂器到印尼、巴厘島、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地錄音,像是在鐘乳石洞、稻田、火山口旁捕捉聲音,就是要把旅程中的文化與自然,真實地放進歌曲裡。
我從小在北投大屯山附近長大,上幼稚園時,都要走一小段山路上去,下課就跟著阿嬤一路晃下來;放假時,會跟山裡面親戚或鄰居的小朋友,一起挖土、玩昆蟲。長大之後,只要從臺北市區回北投的路上,看到大屯山、陽明山,就有種「回家了」的感覺。 我的家庭也很喜歡親近自然,假日會帶野餐墊去擎天岡野餐,或是去魚路古道、天母古道健行,我在山裡度過了很多童年,我想,這也是為什麼我總是會習慣地往大自然 裡走去。
前幾年因為搬到比較大的空間,開始想要放些木頭在家裡作為擺飾,讓空間看起來更溫暖,除了加入像「愛木成痴」這樣的社團之外,也會關注水庫即時消息,因為有時在洩洪後,他們會開放民眾撿拾漂流木。(除了規定的開放時間之外,平常是不可以隨便撿回家的喔!) 也因為我在打鼓,就想自己削一雙屬於臺灣的鼓棒,開始研究不同木頭的特性,或是去南投、三義的木雕工房參加體驗課程。不同木材種類做的鼓棒,打出來的聲音、可營造的感覺都不一樣,例如檜木的材質鬆軟,打起來就會有種中空、甜甜的聲音,很適合爵士樂,或輕小音量的演奏;而肖楠因為很堅硬,很適合做很壯闊的聲音,像是搖滾樂、打落地鼓。 肖楠之所以特別堅硬,是因為他生長的環境都是高山、峭壁,樹根經常被地層變動擠壓變形,受傷之後又會重新長起來,就會變成「樹瘤」,就像是我們身體受傷結痂一樣。後來人們才發現,樹瘤切開來後,會有很多漂亮的花紋在上面⸺那彷彿是它曾經歷的苦難所凝結而成的結晶,對我來說,這是一種非常浪漫的寓意。但也因此有很多山老鼠會為了牟利而非法砍伐肖楠,這也是一個我們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。
第一張專輯時,因為創作主題就是環島找聲音。有次跟朋友到花蓮,一個靠近太魯閣族的藝術村駐村,剛好遇到部落裡的人,在為部落傳統歌謠大賽練習他們的傳統樂器:木琴、木鼓,於是開始跟他們請教,也希望可以把他們傳統的樂器聲放進專輯裡。 後來,這兩個樂器的聲音就有收錄專輯中,在一首叫〈Rainbow〉的序曲,還融合了印尼、西非的打擊樂器甘美朗、巴拉風的聲音。對我來說,這些樂器都有種儀式感與神聖性,能跟天地之間產生某種連結,而那正是我想要在序曲中傳達的。 另外,也曾使用來自卑南族的人面造型警鈴⸺臀鈴taoriul,這個警鈴過去是在發生事故時使用,負責通知的人會將臀鈴繫在腰間,快速奔跑發出響聲,以通報族人。 後來,我也在錄音室裡繫上臀鈴,透來回走動製造聲音,並收錄在歌曲〈巫女〉最後的變奏中,那是一段帶有迷惘與迷幻氛圍的段落。對我而言,它原本的用途、使用方式,跟所帶來的畫面感,都是很重要的。
退伍之後,我先是搬到板橋、中和這幾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,其實活動起來心裡壓力滿大。後來我開始騎車往山裡跑,像是三峽的拉拉山、復興鄉,或是去烏來。對我來講,就像是一種定期的自我減壓。 有時候覺得身為臺北人很幸運,雖然生活壓力很大,但只要騎車或坐車大約20、30分鐘,就可以到附近山區,好好地喘一口氣。
接下來我想做一張給阿嬤的專輯。這三年我都在不同國家巡迴,每次抵達新地方,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阿嬤,很想把我看到的這個世界,用阿嬤能理解的方式分享給她。 阿嬤是我的忠實觀眾,每次有Podcast訪談我都會貼給她,但她卻不太常聽我的音樂,因為她說聽不太懂,只會有一首臺語歌她會一聽再聽。所以我想做一張很簡單的專輯,用我們平常溝通的語言,加上一些她熟悉的元素,讓她也能享受這份創作。
記得現在的樣子,還有那些快樂的時刻,永遠都不要忘記作夢。到現在,我還是每天在作夢,甚至會把夢記錄下來,希望你們也一樣,每一天都不要停止。